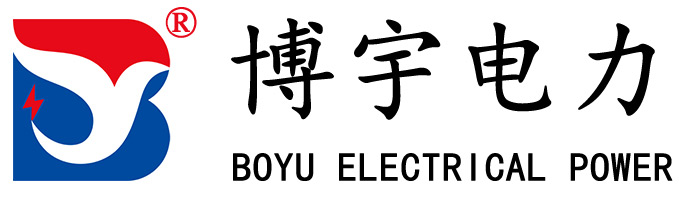近些年,“跨年”蓋過了過元旦的風頭,它以公元紀年最后一天迎接新年第一天為噱頭,成就了許多衛視節目的新創意,并逐漸成為一座城市的狂歡儀式。“玩不好‘跨年’,可能輸掉新的一年”,意在說明“跨年”很重要。
跟“光棍節”一樣,“跨年”充滿了青春元素。中老人淡定得多,但時常擋不住裹挾。筆者就有此類打算,不一定是沖著那家衛視的跨年晚會,或哪里的燈光秀,在元旦前夜,去觀光東湖綠道,或漫步中山大道,因為那更適合中老年人的怡情懷舊。
元旦的最早記憶,大概是讀初中時,每年“兩報一刊元旦社論”,是貧窮年代留下的精神記憶。以后數十年,我竟然也有自己的“跨年”。第一次,十八歲那年的最后一天,我穿上綠軍裝第一次乘火車北上,深夜趕到了中原腹地某部,次日就是新的一年。這一跨,決定了我從軍之旅和后來轉業進城的人生道路。第二次,則是邂逅了出生在一年最后一天的人——即我的妻子。成家后,每年都能以慶生的形式迎新。除了孩子兒時以此為由“打秋風”,近些年,我們一般是元旦前一天看央視的“新年音樂晚會”,作為次日看“維也納新年音樂會”的預熱。由于音樂素養使然,每年不過是被那幾首大家耳熟能詳的名曲感染一番而已。
上世紀最后一晚,我們把岳父母請到附近一家專門吃野生腳魚的酒店。二老不肯我們在外花錢,我給出理由,除了妻子生日,就是“跨世紀”,人生不會有第二次。花六百多元,只說花了兩百多元。老人連說劃得來。十幾年后我忘了,可妻子記得。看來,這個錢花得確實劃得來。
“跨年”最早似乎發源紐約曼哈頓,新世紀在國內興起。對比中國除夕守夜迎春節,前者是克隆還是異曲同工,我不得而知,卻多個理由長點文化自信。為什么中華文明在世界上唯一延綿不斷,或許從這窺斑見豹。中國歷史奔流不息,任何時點都不會抽刀斷水前后兩別。
跨的意向,是在道上披荊斬棘,繼往開來。武漢在2017年到來之前,開街盛裝的中山大道,那是禮敬歷史;開通軌道機場線,那是聯通世界;開啟BRT公交,那是時代節奏;開放東湖綠道,那是回歸自然。長江兩岸,經典比肩;老少市民,各得其所。與其說這是年終巨獻,不如說這是江城風范的“跨年”。